AIGC(AI-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指基于生成对抗网络(GAN)、大型预训练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方法,通过对已有数据进行学习和模式识别,以适当的泛化能力生成的相关内容。近年来,随着AI技术的发展,以AlphaGo、ChatGPT、文心一言为代表的的生成式AI,在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通过训练模型和大量数据的学习,AIGC可以根据输入的条件或指令,生成与之相关的内容,甚至完成“智能洗稿”,将搜索的内容通过同义词替换等形式,采用不同的文字组合、遣词造句表达相同的观点。从作品的表现形式看,其可以满足法律对分类作品的要求,如下图由“Creative Machine”机器自动算法生成的《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图画,能够满足《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美术作品的规定的要件之: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有审美意义、平面的造型艺术设计。基于此,本文拟围绕形式上已符合作品表达方式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讨论其是否具备可版权性。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独创性的认定,二是从产生路径区分“人工智能生成的”与“人工智能辅助完成的”结果,三是创作主体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来自:《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载citylawforum网,https://blogs.city.ac.uk/citylawforum/2022/06/21/ai-and-ip-building-a-research-agenda/
一、依据既定规则、算法、模板产生的内容不具备独创性
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的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独创性是构成作品必不可少的要件。其中,“独”是指“独立创作、源于本人”,可以表现为两种情形:其一是从无到有进行独立创作;其二是对已有作品进行在创作。而“创”是指作品必须是智力创作成果,不要求达到艺术创作的高度,但是应当给到作者智力创作的空间,体现作者个性化的表达。1
现阶段,从人工智能生产内容的单一过程看,其仅涉及某种算法、规则和模板的直接应用,其中没有作者个性化表达的介入;而在此之前人工智能的算法、规则和模板的确定是有个性化表达参与的。以上文提及的《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图画的生成路径为例,2Steven Thaler开发了嵌有AI技术、能够产生创造性输出的计算机系统“Creative Machine”,在用户输入指令后生成了图画。计算机系统的生成包含了作者的个性化表达,例如希望生成的是什么类型的图画,输入的元素内容有哪些,提供了哪些数据供机器进行学习,让机器在接收到哪些指令后可以生成何种类型的产物.......这些都是作者投射了个人编排与选择的内容,但是机器所带有的算法、规则、模板一旦形成,无论是谁输入了相同的指令,所生成的表达内容都是有限的。这就好像,摄影师让拍摄对象在镜头前摆好姿势,选择和安排照片中的服饰、窗帘和其他各种配件,安排拍摄对象呈现出优美的轮廓,处理好光线及阴影后,调整好照相机的位置,那么不管是谁摁下了开关,都可以拍摄出表达形式较为相似的照片。
因此,算法、规则和模板是否为智力成果,与应用算法、规则和模板的过程是否属于智力创作,产生的结果能否构成作品并无必然联系。如果将它们应用于原始材料之后,只要方法正确,无论由何人实施,获得的结果具有唯一性,就排除了实施者发挥聪明才智的可能性,导致相应的结果无法具有个性化的特征,从而不符合独创性的要求。3
二、应从产生路径区分“人工智能生成的”与“人工智能辅助完成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经修订的关于知识产权政策和人工智能问题的议题文件》明确指出:“‘人工智能生成的’与‘人工智能自主创造的’是可以互替使用的术语,系指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由人工智能生成产出。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可以在运行期间改变其行为,以应对意料之外的信息或事件。前者要与‘人工智能辅助完成的’产出加以区分,后者需要大量人类干预和/或引导”。4如上文所述, 前者因仅为算法、规则和模板直接生成的结果,不符合独创性的要求;后者相当于人类将人工智能用作工具创作作品,在能够呈现作者创作空间且满足其他要件的情况下可以在认定为作品,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判断时依旧要从产生路径入手。
以我国产生的第二起涉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侵权诉讼为例,5腾讯公司认为他人擅自传播其人工智能写作软件Dreamwriter生成的新闻报道,侵犯其著作权。在该案中,法院将涉案文章的独创性认定与涉案文章的生成过程是否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化选择、判断及技巧等因素拆分开来认定。首先,法院认定涉案文章具备了独创性,原因在于腾讯主创团队人员运用Dreamwriter软件生成的内容,在外在表现上符合文字作品的形势要求,表现的内容体现出对当天上午相关股市信息、数据的选择、分析、判断,文章结构合理、表达逻辑清晰。其次,在认定涉案文章生成过程时,法院认为是“人工智能辅助完成的”,“涉案文章的生成过程主要经历数据服务、触发和写作、智能校验和智能分发四个环节。在上述环节中,数据类型的输入与数据格式的处理、触发条件的设定、文章框架模板的选择和语料的设定、智能校验算法模型的训练等均由主创团队相关人员选择与安排。……原告主创团队相关人员的上述选择与安排符合著作权法关于创作的要求,……应当将其纳入涉案文章的创作过程。……本院认定涉案文章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文字作品。”
法院在论述时有提及:“若仅将Dreamwriter软件自动运行的过程视为创作过程,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将计算机软件视为创作的主体,这与客观情况不服,也有失公允”,而为了论证法院在第一部分认定的涉案文章具备的独创性,其将涉案文章的生成过程扩大分析,认为“在数据输入、触发条件设定、模板和语料风格的取舍上的安排与选择属于与涉案文章的特定表现形式之间具有直接联系的智力活动……该文章的表现形式是由原告主创团队相关人员个性化的安排与选择所决定的,其表现形式并非唯一,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由上文可以看出,仅根据内容生成过程看,Dreamwriter软件自动生成涉案文章的两分钟就是“创作过程”,没有人的参与,仅仅是计算机软件运行既定的规则、算法和模板的结果,只是为了不将“计算机软件视为‘创作’的主体”,将范围扩大,将人类智力活动的过程也纳入其中,实则混淆了两个问题:一是谁研发了人工智能的算法、规则和模板?二是谁生成了构成涉案新闻报道的文字组合、遣词造句?显然,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腾讯公司的主创团队”,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第二个问题也应当做出相同的回答。回到文章观点,涉案文章的生成仅仅是计算机软件运行的结果,这一过程并没有体现作者的智力创造与选择,不存在个性化表达的空间,该结果不具有独创性,该过程也不应当认定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作”行为。因此,应当从人工智能生成结果的产生路径认定实际情况,区分“人工智能生成的”与“人工智能辅助完成的”,不应当因果倒置,为了论证出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就将实则仅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结果认定为“人工智能辅助完成的”。
当然,若作品是在“人工智能辅助完成的”,则作者可以主张受到版权法的保护。美国艺术家克里斯蒂娜・卡什塔诺娃 (Kristina Kashtanova)最初为漫画《Zarya of the Dawn》申请版权登记时,并没有区分AI生成部分和艺术家创作的部分,该书在美国获得了版权登记。后来,美国版权局通过艺术家网络发帖发现作者创作时使用Midjourney软件生成了已登记作品中的部分内容,随后以该作品缺少人类作者为由拒绝注册,原因是版权法仅保护“人类作者身份的作品”。在作者申请复议后,版权局在2023年2月21日发布新的决定,准许《Zarya of the Dawn》的整体登记,但同时明确排除AI生成部分的可版权性,新的注册范围修改为“作者创作的内容和对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的选择、协调和安排”。6
三、非自然人或法人创作的作品不能认定为作品的主体
我国《著作权法》第2条将享有著作权的主体限定为“中国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和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无国籍人”, 印证了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即文学、艺术作品等由信息构成的成果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律上的财产,是出于特定公共利益的需要。我国《著作权法》第1条开宗明义地明晰了这种公共政策——“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可见,只有人的行为才可能为著作权法所鼓励。如上文所述,现有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还停留在某种算法、规则和模板的直接应用,不具备独创性;假设AI技术真的突破了这一限制,能够在纳入创作者个性化的表达后生成“作品”,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依旧无法将AI软件认定为作者。以“猕猴自拍案”为例,7动物当然具备一定的智力,其通过观察游客行为学会了按下照相机的快门拍照,甚至学会了在镜头前龇牙微笑的动作,在其中呈现了其个性化的表达,但正因为猕猴不属于“人”不具备版权法保护的基础,故不能据此将猕猴认定为“作者”,AI软件也是一样的。在菲林律师事务所诉百度网讯公司案中,8法院认为菲林律师事务所利用“威科先行库”软件自动生成的分析报告虽然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但由于其并非由自然人或法人创作完成,故不能认定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在该案中,法院强调了自然人的创作行为对作品的决定作用,排除了非自然人创作作品的可能性。
国内外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实践案例表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必须是人类创作完成的智力创造成果,这既是从立法目的出发的结果,也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权利主体对权利义务的承担,因为只有法律认可的自然人或法人主体才能行使权利、承担义务,也即非人类智力创造成果不具备版权保护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结 论
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发展,或许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还有更多新类型的创作成果将会出现。《著作权法》的保护路径并非是保护新技术生成内容的唯一方式,但如果要考虑这些内容的可版权性,应当立足于现存法律规定的要件进行判断,即只有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备独创性,并能够以某中有形形式复制的人类智力成果,才具备可版权性。
注 释
1.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版,第24-41页。
2.THALER v.PERLMUTTER (1:22-cv-01564-BAH) District Court, District of Columbia, CourtListener,CourtListene(Aug.18,2023), https://www.courtlistener.com/docket/63356475/thaler-v-perlmutter/.
3.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5期。
4.《王迁:ChatGPT生成物与“猕猴自拍”无异,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争鸣》,载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2023-08-31, https://mp.weixin.qq.com/s/8hShUOaTHn5-TedaUyMdXA。
5.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305民初14010号。
6.Zarya of the Dawn (VAu001480196) at 2, Copyright.gov(Feb.21,2023), https://www.copyright.gov/docs/zarya-of-the-dawn.pdf.
7.Naruto v. David John Slater et al, No. 3:2015cv04324 - Document 45 (N.D. Cal. 2016), JUSTIA US Law, https://law.justia.com/cases/federal/district-courts/california/candce/3:2015cv04324/291324/45/, 二审判决对此予以赞同。
8.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73民终2030号。
联系人:张律师
联系方式 ①:13923885590(同微信号)
联系方式 ②:13924628232
邮箱:info@shidingip.com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新田社区福中路17号 中国国际人才大厦808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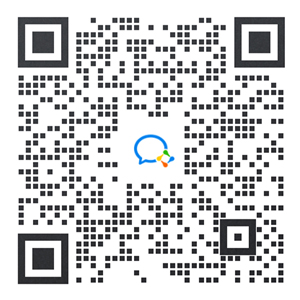

跨境电商侵权和解申诉交流群
张勇律师
个人微信
跨境电商
公众号


